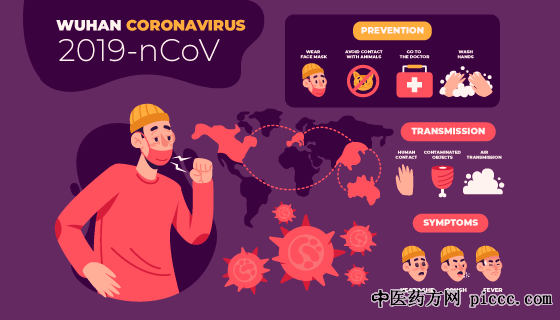|
基于特有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以及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崇尚,有史以来,日本保存了大量中国书籍、药品、文物等,客观上对保护、传承中国文化发挥了作用。近年来,日本国立图书馆以及多数大学图书馆将所藏中国文献逐渐在网络公开,方便读者查阅及研究。
日本一直热衷于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而且持续千数百年,实属一种罕见的历史现象。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鼎盛时期,尤其中后期,研究水准可谓登峰造极,硕果累累。江户后期至明治初期,随着西学东渐加速,汉方医学与其他文化同样发生方向性改变。尽管优秀的汉方医家仍然不遗余力地研究著书,却难以得到时代及当权者赏识,能够完整保全稿本,已属劫后余生。有幸后人识其价值,方使之重见天日。
日本保存着大量重要的医药抄本及稿本,早期完成的有丹波康赖的《医心方》、梶原性全的《万安方》《顿医抄》、有林的《福田方》等稿本著作,收载了中国唐宋时期大量医书内容,为研究中国古典医籍提供了重要文献。另有医籍抄本如《明堂经》《小品方》《太素》《真本千金方》《太平圣惠方》等中国散佚的医书,为中国医籍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日本亦保存了大量作者手稿,以江户中后期稿本为多。近30年来,笔者翻阅了日本医家诸多手稿,并已整理出版了20余部稿本医书。本文主要介绍江户时期最后一位汉方医学者森立之(1807-1885)及其遗留稿本,并探讨其对于研究中国医学古籍的价值。
笔耕不辍 著述等身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森立之少年拜师求学,青年锐意探索,中年落魄相阳,老年囊中羞涩,而生涯笔耕不辍,编撰著作180余种,但大多未曾刊行,以稿本留存。森立之飘逸遒劲的字体,独特翔实的考证,涌动着难以抵抗的魅力。森立之有《自作寿藏之纸碑》一文,记述了流放期间悲喜感慨:“此间十二年,辛苦不可胜言,然乐亦在其中。何者?半为儒半为医,居则以教授幼童为业,目读奇籍,耳听异闻。出则手握刀圭,足涉山川,无论内外二科,或为收生,或为整骨……又入山采药,下溪钓鱼。有《桂川诗集》,有《游相医话》,其行乐中大有大裨益于正名学者,皆一一笔录,以备后考,竟至一百余卷。其他如《神农本草经》《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扁鹊传》《四时经》《奇疾方》等,并皆有考注。余壮时落魄于相阳十余年,刀圭余暇,跋涉山川,与樵渔为邻,故于实际略有所得,是亦不幸中之幸也。”
可见流放的12年间,森立之完成了多部著作,尤其是通过临证诊病、入山采药,甚至栽培植物等实践活动,编撰了医方、医话、本草类著作。这是身居江户读书、讲学所难以获得的成果,为其后30余年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森立之百余部著述中,用心最钻、费时最久、成果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他的系列《攷注》,每部皆百万字大作。
《伤寒论攷注》 该书卷三十末附记:“此书起业于庆应元乙丑年四月,今兹至戊辰二月,中间凡三年,退食刀圭,奔走余闲,夜以继日,遂得脱稿矣。余五十年来精神之所专注,唯在此之三十卷中,如其家说秘诀,其理玄妙幽微,盖非其人则叵传。仲景以后以心传心之至意,久失其传,注家皆就文字上而解说,但是升堂而未入室之徒耳。今看破其偏陋而归于临症实诣之地,则仲景之书可始读而可始施用于今日也。六十二翁立之再录。”据此可知,该书完成于庆应元年(1865年)至庆应四年(1868年)三年之间,然而如此一部巨帙,绝不是短短三年能够编成的,而是历经半个世纪凝聚的结晶。
《金匮要略攷注》 该书编著于安政丙辰年(1856年)至文久癸亥年(1863年)之间,成书早于《伤寒论攷注》,二书同时撰写。《金匮要略攷注》全三卷二十五篇,现存十二篇,系弟子青山道醇摹写本。《金匮要略攷注·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识文:“文久三年癸亥上巳后一日灯下书 养竹老人立之 此日从清心院尼公驾,至于福井侯常磐桥内上邸。明后六日松平春岳君后宫悉发此地,移于越前福井城中,今日方是离席离宴之会也。日晩归舍诏例亲笔研,记此以为后日之备忘耳。”可见森立之无一日辍笔,无一刻忘怀,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完成了等身之作。
《素问攷注》 该书编著于1860年至1864年,这是森立之集19世纪以前中日学者《素问》研究大成之作。《素问攷注》除运气七篇和遗篇之外,每篇标题后均注明《甲乙经》《太素》及全元起所记内容,同时收录日本学者见解。森立之大量引用中国经、史、子、集著作及字书、韵书、训诂专书,缜密考证,阐明了大量疑难问题,为中日两国研究《素问》编撰了一部不朽著作。
《本草经攷注》 该书编纂可以追溯至森立之青年时代,正如该书序文中所云:“余自幼枕藉此经,萤雪余光,手不舍笔,盖卅年于此矣。花间月下,在浮白飞觞之间,未尝不一念及此,稍稍有所发明,窃谓得古本草之微,著为此编,以俟后之君子。安政五年岁次戊午二月廿日五更灯下书。枳园拙者源立之。”年过半百的森立之严冬二月五更大作杀青,可以想象胸中一定是火热的。
缜密考述 质量兼优
森立之以超人的勤奋与坚持,编撰了质量兼优的著作,至今仍无出其右者。引用文献全面,考证精详,见解独特,文字秀逸。观其书,赏心悦目;读其文,慨叹折服。江户学者虽然熟知传世文献,但未曾得见出土资料,而森立之诸多解疑考证,却均得到百年后出土文献的证实。仅举数例如下。
《素问攷注·阴阳应象大论》中,森立之认为“七损八益”并非男女“七七、八八”说,乃指房中术。森案云:七损八益,古来注家意见各出,皆出于臆断,不足据。王注以为房事,盖有所受而言。今得《医心方》,而千古疑义一时冰解。但其言猥杂,故王氏不详录也。
《素问攷注·阴阳别论篇》:“肺之肾,谓之重阴。”森案云:“肺”当“肝”字之讹也。《素问》《大素》皆不正也。肝之肾者,子乘母也,即相生之变也。若肺之肾,则与前“生阳”同义。可笑。盖重阴者,阴病,虚病之重甚者。重,去声。未至死阴之危也,故非死病也。“肺”作“肝”,则五行咸通之理。此句前注皆叵从。
《伤寒论攷注》中森立之考证计数药物,认为唐代以前皆云“物”,唐以后“物”“味”混用。药量由“等”演变为“分等”“等分”等。森案云:凡云“物”者皆是古言,云“味”者后世改书者。每方后并云“右几味”者非古式,唐已上方后文例非一,盖所传各异故也。《医心方》所引葛氏、范汪、僧深、《小品》等皆方后云“凡几物”,独引《千金方》皆云“几味”。引《子母秘录》亦作“右几味”,引张文仲、僧深方共作“右几物”。据此则方后文例,唐已上不一定,然则每方题云“右几味”者,昉于王焘《外台秘要》欤。但《外台》宋板之外,李唐遗卷无传本,则亦为难定矣。《千金》《外台》宋板共存,而共题云“右几味”,与《伤寒论》相同,则如此一定者,殆昉于宋板欤。笔者考察出土文献相关记述,皆用“物”而无一用“味”者,证明森立之依据传世文献已得出正确结论。
关于《伤寒论》中桂枝汤条“鼻鸣”,注家皆以为鼻塞而息鸣者,必鼻干。《伤寒例》云:“二日阳明受之,其脉侠鼻,故鼻干……因考鼻鸣者,谓喷嚏也。凡有声而可听之证皆称曰鸣,如喘鸣、肠鸣、耳鸣是也。喷嚏亦有声,宜称鼻鸣而可也。”并引用《说文》《释名》、慧琳的《一切经音义》、《苍颉篇》等中国字书对于“鼻鸣”的注释,以及日本《万叶集》《和名抄》等日本对于“鼻鸣”的训读。又分析《伤寒论》《素问·热论》《灵枢·口问篇》《病源·虚劳候》《金匮·咳篇》中关于“鼻鸣”的生理病机,求证“鼻鸣”当指喷嚏之意。森立之认为,凡仲景书中多用古言俗呼,如称厥冷为四逆,称大便为更衣,气上冲之病谓之奔豚,半身不遂之证谓之中风之类是也。谓嚏为鼻鸣,恐亦此例。
《本草序例》云:“钱五匕者,今五铢钱边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为度。”森案云:“钱五匕”不可读。《顿医抄》卷第四十九引《本草》载此文,“钱五匕”作“钱五上”。《医心方》卷第一引《本草经》亦同。又《医心方》引他书,“钱匕”字皆作“钱上”,无一作“匕”者。唯方寸匕则皆作“匕”,亦无一作“上”者。因考《证类本草》成于宋人手,校改颇多,此“钱五匕”,殆亦连上文“方寸匕”而误,宜从李唐遗卷改作“钱五上”。《顿医抄》每据《新修本草》,则《新修》尚作“钱五上”可知矣。盖彼土自宋板一出,钞本渐失传,如皇国除宋板元钞外,间存唐传卷子钞本,得以订宋以后误字、脱字,不遑枚举。如《序例》中门冬、远志,别有君目,《证类》误作君臣。俗方五石散,《证类》误作玉石散之类是也。又今本《肘后方》云:“凡云钱匕者,以大钱上全抄之。若云半钱,则是一钱抄取一边尔。并用五铢钱也。”此文足以补序例之阙,而“钱上”已讹作“钱匕”,唯云“大钱上”,尚不误。盖宋人校改未遍者也。《外台》卷二十引《小品》麝香散方后云:“酒服钱半边匕,老小钱边三分匕。”此二“匕”字亦宜改作“上”。《医心方》卷二十一引《小品方》治妬乳方后云:“以酱服钱一边五文上。”可以征也。“钱五上”最早见载于5世纪的《本草序例》,其后在传抄过程中出现讹误。据考,敦煌开元六年(718年)抄本将“钱五上”写作“钱五匕”,又逐渐出现“钱五匕”作“五钱匕”,“钱上”写作“钱匕”等混乱现象,现今约定俗成为“钱五匕”或“钱匕”。
森立之著作中卓越的考证案例举不胜举,但因其稿本一直封尘于书库中,难以借阅,又因现今日本汉方界能够读懂森立之的学者已屈指可数。好在20年前首次由学苑出版社排印出版后,受到读者好评,方便学习研究。当然,稿本排印后,原稿某些内容不得已被删除,仅依据印本难以全面反映作者真意。手稿是书籍版本的原创形式,亦可称为“孤本”,不仅在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也是书法艺术上的一座丰富宝库,值得深入研究。(郭秀梅)
(该文转载自《中医药文化》2020年第二期,编辑时有删减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