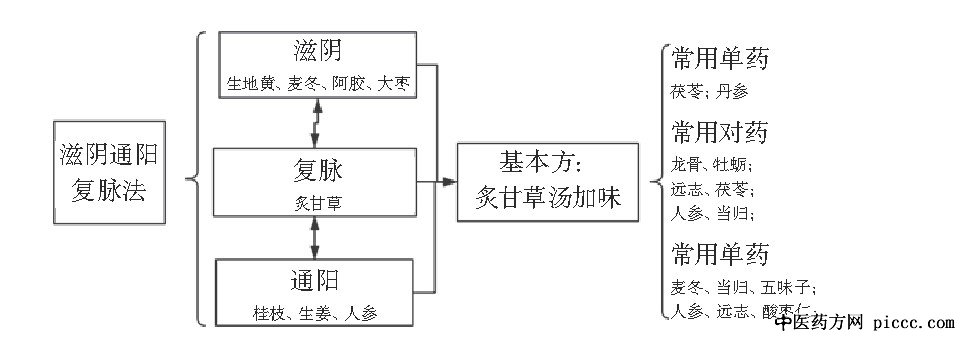|
长期以来,有一些人认为青年时代的鲁迅在日本受过现代医学的洗礼,回国后在《呐喊·自序》《父亲的病》等文中,又对中医进行批判。这样一来,似乎他对中医药典籍是绝无兴趣问津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鲁迅先生曾说:“我后来也看看中医的医药书。”(《坟·从胡须说到牙齿》)《本草纲目》就是他常置于案头翻阅的中医书。
鲁迅早期所写的小说、短评、论文,常提到《本草纲目》的内容。例如,《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的嘴提到“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在《热风·三十三》中也涉及《本草纲目》。1933年6月,鲁迅写道:“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举出令人信服的实例,否定了积久相传的“神农尝百草”的唯心主义论调,肯定了医药也是由“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他一再强调人们现在能够懂得许多药物的性能,乃是古代劳动人民付出血的代价而取得的经验。“……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伪自由书·推背图》)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草纲目》是人类向自然进军,以血为代价,日日月月累积起来的一部庞大著作。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在这里也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实证。
鲁迅不但常翻阅《本草纲目》,而且常和一些对《本草纲目》颇有研究的人谈论它。许广平回忆道:“记得他在上海的时候,常常和周建人先生相见,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要谈话。谈话内容,其中就会从植物学谈到《本草纲目》。”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中写道:“如《本草纲目》……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拉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他还在《坟·看镜有感》中写道:“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心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可见,鲁迅对这《本草纲目》有非同一般的重视。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提到一只由上海老药铺生产的“双料乌鸡白凤丸”的匣子。周海婴回忆说:“母亲(许广平)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连西医也感到吃惊。这种中药丸,后来父母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致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结果也治愈了。”周海婴据此评论说:“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在书中周海婴还提到,他幼年在上海患严重哮喘,各种药都不灵。经人介绍,鲁迅在脸盆内用开水调芥末二两,浸入一条毛巾。然后将毛巾拧干,热敷于患儿背部,疗效大好。这显然是一种民间中医疗法。鲁迅亲自操作,屡试不爽,这也应该说是他对中医药的一种态度吧!
如此看来,鲁迅并不反对中医,只是批判庸医。(杨晓光 赵春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