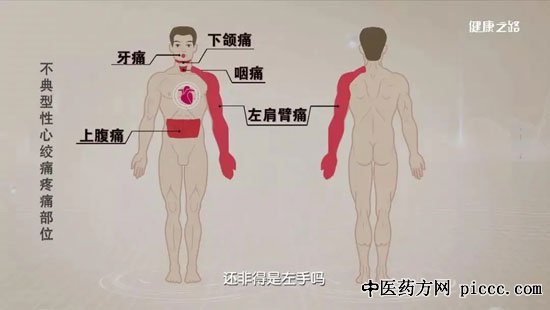|
“深浅在志,远近若一”是《黄帝内经·宝命全形论》里的一句话,原意是指行针之时心手合一、乘物游心、医者对患者感同身受的契合状态。本文借用这句话意在表达:人本身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只有把食物腐熟到极致才能真正全面地吸收水谷精微;对待《黄帝内经》等经典,也要烂熟于胸,才能真正把握“活的思想”。那么,对经典文本特征的充分了解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文本而言,《黄帝内经》的表达方式显然不是分析型的,因为其运用的方法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
不仅《黄帝内经》,《论语》和《道德经》也基本存在这样的表达特点。在一次会议上,俄罗斯学者克鲁申斯基曾经这样阐述:《论语》的篇和篇、段和段,甚至句子和句子之间这种看起来好像无关联的表达方式,是受到《易经》里卦和卦、爻和爻排列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样适合对《黄帝内经》的解读。作为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易经》的显性和隐性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不然也称不上“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关于“易医”关系,很早就有“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易医同源”等说法,本文仅从文本角度作探讨。《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论语》等经典的表达特点可归结为:指点、叙述(呈现)和互文见义,而不是指实、分析和下定义。
“指点”的意义在于“以有知无”
“指点”基础上的“点而不破”的表达方式让《黄帝内经》等经典具备无限的张力,从而历久弥新。千百年来我们面对同样的经典,但理解和认识结果差别很大。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研究学习中医者不可须臾离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这种能够跨越时空、常读常新的特质与“点而不破”的文本特征具备无限的张力直接相关。
“指点”与“暗示”密切联系,最高明的指点是“点到即止”“点而不破”,因为一旦“点破”就等于把问题“说死”了,离被淘汰就不远了。中医学关注的永远是“活着的人”,是灵与肉的结合。越是高妙之处越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大概与先贤对于“生命”的认知有关:肉体和精神对于生命都是不可或缺的;有形的实体可以用语言表达清楚,但要把一个人内在的、与生命体验相关的精神层面明确无误地阐述出来恐怕难以做到;一个没有了精神支撑的肉体不会存在很长时间。这就是中国哲学和中医学里的阴阳关系,即“有”和“无”的关系。经络和穴道概念的产生与这种认知直接相关。“指点”的意义在于“以有知无”。经典之所以历久弥新,不仅仅在于传承知识,更在于传承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
作为传统社会的“至圣先师”,孔子主张的方法论不仅可以治国,还可以“治人”“治病”,具有普适性,且三者一脉相承。对于经典的学习,孔子主张学思并重。“学”是掌握知识,“思”是把知识与人生结合起来加以升华借以形成“三观”,然后再关照自己的人生日用。因为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在“指点”中每个人的收获是不一样的,所以易学、道家、儒家、医家都把人分为不同层次。易学中阴阳符号及其所组成的卦是最典型的“指点”方式。有人从其所表征的阴阳之理中参悟到人生“大道”“德义”和治国安邦的道理,有人则流于占卜等“小道”。同样是《老子》,有人看到的是明哲保身的存身处世之道,有人得出休养生息的治国大略。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黑格尔则认为:只是一位智者在进行道德伦理问题的说教(黑格尔显然不了解《论语》表达思想的特质)。面对同样的中医经典,有的人成为“上工”甚至“神医”,外可造福社会,内可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有一些人成为单纯以牟利为目的甚至危害世人的“庸医”。这种结果的巨大差异与《黄帝内经》等经典的“指点”而不是“指实”的表达方式直接相关。
指点的方式给我们最初的感觉往往是离题千里,不知所云。
就《易经》来看,其基本组成是阴阳两个符号。阴阳符号只有放在三画卦或者六画卦之中,才能反映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和阴阳之气消长流变的动态过程,这就是中医学里一直在强调的动态中的整体观。正如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所言:“语言符号系统或曰施指系统是纯形式的,没有实质用途。因此,这个施指系统的力量乃至其存在都完全依赖于它本身的系统性。”阴阳符号所代表的有名无实的“阴阳”含义只有经过“书读百遍”之后才能逐渐体会得透彻,也才能在医学实践中运用自如。老子在《道德经》里也明知自己是在“说不可说之说”但又“不得不说”,已经暗示出《道德经》作为一个文本仅是“悟道”的一个途径、一种工具。《论语》开篇首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种安排是意味深长的:在反复的温习、实习和见习之后,自然能逐渐体会到经典的微言大义,这是超越具体知识之上的境界提升和心胸拓展,其中收获的快乐莫可名状;这本身就是养生,就是“治未病”。《易传》中有“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命题。“言”和“象”都是工具,我们离不开工具,但不要拘泥于工具。所以,这种指点的表达方式在诞生之初就注意到要防止人的行为出现“异化”,即人不应当成为自己所制造工具的“奴隶”。这种认知模式和方法论对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影响极深,而与注重外在工具和仪器研发的西医学大相径庭。
“六经皆器”告诉我们,不仅仅语言文字是工具,古代经典也是一种工具,我们需要工具的帮助,但要超越工具本身,不然就容易出现“异化”和“僵化”的状况。这也是中、西医学在诊疗中的一个差异所在。
“叙述”是展示型的辩证逻辑
“叙述”(呈现)的方式是《黄帝内经》等经典象思维的基本展现方式。其背后不是分析型的形式逻辑,而是展示型的辩证逻辑。只是呈现,结论由自己作出。
叙述的方式在于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对事物呈现出来的“象”进行描述或展示,而不是极力表达自己的观点,即“述而不作”。《易经》《道德经》《论语》《黄帝内经》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表达方式。
一如《易经》,通过阴阳六个爻形成一卦,从下到上依次是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从“初”到“上”而不是从“一”到“六”,说明每一卦都表达的是一个“终始之道”,是一个圆形模式而非线性模式。每一卦的阴阳爻的数量和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可以比拟自然界中的具体时空和具体存在物,包括病灶。六十四卦代表宇宙大时空,每一卦代表一个具体而微的小时空。这就是呈现,是典型的象思维。二如《道德经》,整体是围绕着核心概念“道”来描述的,哪怕是最重要的命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采用的是描述或呈现而非分析的方式。三如《论语》,其“仁者爱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同样是这种白描手法。再如《黄帝内经》:“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至于怎样“生肝”,怎样“主目”并不去分析。因为只要采用分析的方式,就需要概念本身具备确定的内涵,不能有歧义,前提就需要明确这个概念,也就是下定义。下定义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借助概念的种差关系对一个范畴进行明确界定。但形式逻辑本身是有漏洞的,西方“芝诺悖论”里“飞矢不动”“阿基利斯永远赶不上在他前面跑的一只乌龟”等早已揭示了这种缺陷。那么,以形式逻辑为立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就是很自然的结论。所以,科学主义不足取,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大力提倡。
《黄帝内经》之所以采取辩证逻辑而非形式逻辑与“阴阳并重”“有无并举”直接相关。如果只关注到“有”,也就是实体,那么注重外在工具的研发和采用分析的方法论模式就是必然的。但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方式对于“有无并重”且“以有知无”就会显得捉襟见肘。象思维在于把这个客观过程通过描述的方式予以呈现,再结合研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主客观合二为一,通过望闻问切自然能体会到患者内在阴阳之气的异常和五行生克制化的紊乱,这是“物我相应”“内外相应”,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必然落实。由于“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那么“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治好病却很难给患者说清楚”的现象就是正常的。
叙述往往是在动态过程中完成的。叙述者既超然物外又深入其中,这是中医大夫看病的真正状态。这种方式给人最初的感觉往往是“不过如此”,但在叙述中呈现给人们的是动态的整体观。它体现的是个体从属于流变中的整体,而不是刻意放大某个个体以致以偏概全。这就要求我们学习经典一定要善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做到“以点知面”“举一反三”。如果反复做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经典要义便会“跃然呈现于心”。所以娓娓道来的叙述是一种“意识流”的表达方式,借助于“有”,表达的是“无”;借助于“静”,表达的是“动”。这种举重若轻的方式要求我们对待经典需要仔细地、反复地玩味和体悟。
只是呈现,或者叙述,结论由自己作出,这是象思维的特征。
“互文见义”让概念表达余味无穷
“互文见义”是《黄帝内经》等经典表达概念含义最常用的方式,这种外围、圆融的限定概念方法最初感觉是平易简单,但在“书读百遍”后却余味无穷。除了两两对举,“互文”还包括木火土金水等多项对举。
互文见义是先列举一个事物,再对举一个意义相反或相类的事物予以印证或者限制。这与上述指点和叙述的表达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这种表现概念含义的方式在易、孔、医学中是非常突出的。在《道德经》中体现稍差一些,原因在于任何具体存在物都无法与“第一存在物”——“道”比肩而论,但老子还是通过“大盈若冲”“大巧若拙”“高下相倾”等命题有深刻的反映。
互文见义的形成是先贤为解决所运用范畴的多义性、避免产生歧义采取的一种引导方式。显然,这种方式对一个范畴进行限制不是简单、直接的,而是外围、圆融的。由此也造成了中国人说话一般比较“绕”,而欧美等西方人说话则比较直接。这是该种表达方式的世俗化表现。中西医学概念和理念的差别也有似于此。
互文见义在易学中表现为阴、阳爻对举。单纯从“—”符号本身来理解“阳”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对举中,从“--”的角度来解读“—”、从“—”的角度解读“--”,并通过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和上爻叙述式的排列和其中蕴含的“互显”方式,它们所表征的含义才是丰富的、深刻的。通行本六十四卦分为三十二对,排列特点是“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这同样是“互文见义”的表现。理解《论语》中的“君子”和“小人”同样如此。
互文见义的表达方式不仅指两两对举,还包括春夏长夏秋冬、木火土金水、东南中西北、肝心脾肺肾等多项对举,它们之间都是“互显”的关系。这在《黄帝内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果掌握脾胃(土)的病机原理,就一定要关注到肝和胆(木,克土)、心和小肠(火,生土)、肺和大肠(金,土所生)、肾和膀胱(水,土所克)等其他系统。通过五行的生克制化达到平衡的模式是秦汉以后传统文化中方法论的主流形式。其中的关键在于以整体为平台对个体功能形成动态认识。这是随修养、境界不同而不同的,或者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非“知道”且“合于道”者不能如此。其实,无论是两两对举还是多项对举,反映的不仅是二者或多者的对立和差异,更在于二者和多者的统一或共生关系。惟其如此,中医学里的“给邪出路”才可以解释得通。这与西医学里主张直接“消炎杀菌”的理念是很不同的。
孔子主张举一反三,在于面对一个点,能够从三个维度来立体、动态地理解、把握一个事物。而理解中医学的概念,除了长宽高三个纬度,更应该加上一个时间维度,方能理解看似平易的中医学概念究竟有多么深刻。
“对话体”是阴阳观的展现
“对话体”是《黄帝内经》阴阳观在表达方式上的展现,一问一答就是一阴一阳,也是“时的哲学”。
“对话体”的特点在于每一次提问都相当于预设了一个时空,在不同的时空下患者都有不同的表现,医者也应该有不同的应对手段,就如孔子所言“无可无不可”。这与主张建立“金标准”的西医学同样是大异其趣。
俗话说:乱世藏黄金,盛世收古董。如果把西医比作黄金,中医就是古董。二者都是财富,但含义不一样。古董既是财富,又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的样式也成为一种文化。二者的衡量标准也不同,黄金可以重量、数量计,古董只需要保有原来的内容和形式已经是“善莫大焉”。无论用多么现代化的技术给古董刷上“绿漆”,也不能增加它的丝毫价值。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建立,矫枉过正阶段就要过去,中医学也会迎来一个正常发展的时期。(赵荣波)
|